2010年10月14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二十八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教授,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斯坦福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客座研究员,欧洲大学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系教授研究员,国际著名政治学家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与顾肃教授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陈润华、孙国东、吴冠军等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座。他对施密特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表示了诚挚的欢迎,简要介绍了施密特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与顾肃教授。
在正式演讲开始之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向菲利普•施密特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教授”的聘书。接着,施密特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民主化与国家能力”(Democratization and State Capacity)的讲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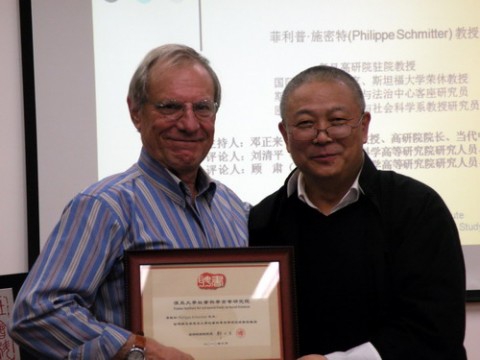
菲利普•施密特教授指出,自1974年以来,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些国家在正在向民主化(democratization)迈进。他的研究所关注的正是这种民主化进程对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影响。
首先,施密特教授对其研究变量进行了说明。在研究中,他将“国家能力”作为自变量,将“民主化”作为因变量。同时,施密特教授指出,国家疆域(state territory)、国际环境(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物质资源(material resources)和合法性(legitimacy)是影响国家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各国情况的不同,国家能力作为因变量具有相对性(relative quality)。
接着,施密特教授阐述了其研究的理论视角。他指出,对于民主化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当今学界存在两种相对的理论视角:一种是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其认为伴随着民主化的进行,民众和社会团体更倾向于通过个体而非公共的方式来获取资源。从而,民主化降低了民众对国家能力的需求。另一种则是保守主义的理论视角,其认为民主化程度越高,民众对国家能力的需求越高。施密特教授指出,他的研究正是围绕“民主如何影响国家能力”这一问题的一般理论视角来进行实证研究,试图找寻问题的真正答案。

基于大量详尽的图表与数据分析,施密特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其分析的具体路径。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施密特教授指出,民主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虚假关系(spurious relation,其关联是由第三个变量“发展/现代化”(development/modernization)引发的。因此,要使用统计方法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发展/现代化”(development/modernization)这一变量进行控制。在研究中,施密特教授重点对那些经历了从传统共产主义集权制度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如俄国和匈牙利)进行了追踪观察。同时,针对现有研究中忽视“国家将资源转换为国家能力的效率”这一变量的倾向,施密特教授在其研究中特别添加了两个影响因素——犯罪和腐败。施密特教授指出,这些国家在政治转型中民主化能力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趋势:即先下滑,而后再上升并渐趋稳定。同时,在这种大的共同变化趋势之下,还存在着两种极端类型的区别:一类国家采取“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s),造成国家能力急剧变动,表现为“眼泪之谷”(the valley of tears)般的波动趋势;另一类国家则通过沟通、协商,国家能力变动相对缓和。
最后,施密特教授对其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伴随经济发展,国家能力倾向于呈现增强态势,这种态势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尤为明显;在那些经历了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型的国家中,民主制度巩固地越迅速,国家能力增强地成效就越大;近年来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的案例中,民主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系相对地十分不明朗。这一方面是因为巩固后起的民主制度更加地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变革之初国家能力的下滑表现地更为急剧。

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高度评价了施密特教授的研究。他指出,施密特教授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方法针对民主转型国家进行了追踪研究,分析了民主化和国家能力之间的关联,其结论很有启发性。刘清平教授非常认同施密特教授关于经济发展、民主和国家能力之间关系的分析结论,并列举了一些实例进行佐证。在对其研究给予肯定的同时,刘教授结主要从“善”(good)与“正当”(right)关系的角度对施密特教授进行了商榷。他认为,斯密特教授关于民主制度增强国家能力以及其关于“善治”(good governance)的一些看法,更多地是强调“善”的一面, 而对“正当性”的关注相对较少。他强调:民主不仅是一个好东西(good thing),而且首先是个对的东西(right thing)。同时他认为,斯密特教授偏重于从抽象的角度来评价国家能力,相对忽视了国家能力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善”与“正当”。在此基础上,刘清平教书指出,在对国家能力和“善治”的研究中,只有同时考虑到“善”与“正当”,才能做到更为全面、更有说服力。

评论嘉宾顾肃教授在对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基础上他指出,施密特教授对民主化与国家能力问题所进行的长期跟踪经验研究对目前的国内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顾教授建议,在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越来越为世界瞩目的情况之下,施密特教授也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典型来进行研究,这对于丰富“民主化与国家能力”关系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顾教授提出,施密特教授在分析过程中,对于结论的原因说明的还不够;他强调,经验研究应该在原因分析上做出更多努力,不然,读者所看到的就只是一些描述性的东西。最后,顾教授特别指出,当前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模式选择的问题,施密特教授对自由民主模式、社会民主模式、保守主义模式和怀旧主义模式的分类研究对中国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围绕两位评论嘉宾的点评,施密特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与感悟。针对“善治”的问题,他认为,在政治制度的转型过程中,规范应被置于权利之上;权利无法做到自我实现,只有借助于好的规范才能够解决各种意见分歧、最终促成权利的实现。在政治制度的模式上,施密特教授认为,实践中很多国家的模式都是一种混合状态(hybrid),而非纯粹的民主或者非民主状态;对这种混合模式进行价值判断必须结合具体的时空环境。施密特教授特别讨论了中国案例的特殊性,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动机与诱因研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在接下来的讨论与提问阶段,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文化在发展、民主化和国家能力的关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研究中应如何处理文化因素的作用?如何看待伊拉克民主进程的未来?有没有考虑过加入其他变量或进行相应的定性研究,以解决目前的研究结论只适用于那些经历了从共产主义集权制度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的局限性?民主的核心要素是什么?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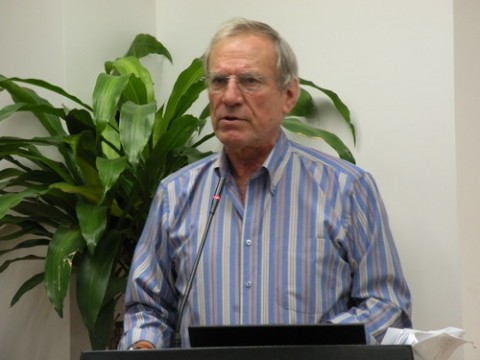
施密特教授对大家的讨论和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他指出,要考察文化的作用必须首先对文化的概念进行区分。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文化,一种是作为区别国家和地区的独特的文化,另一种则是全球化、现代化过程中日益融合的普遍性文化。在关注文化差异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普遍性。具体到发展、民主化和国家能力的研究,首先要关注“发展”这一要素,在此基础上如果解释力仍不足,则可以进一步考察文化差异的影响。在伊拉克的民主进程问题上,施密特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外国力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民主的推进能够通过武力来实现吗?对于其研究结论不能解释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现象的局限性,施密特教授表明,自己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获得一个一般性的理解,而中国和印度实际上属于比较特殊的情况。要突破研究结论的局限性,可以采取非集计型(disaggregate)的方法,对中国和印度这样的特殊个体进行单独考察,将文化、宗教等因素都考虑进去。对于民主的核心要素,具体到与国家能力的关系中来看,在资源的收入渠道上,它能够促使民众自愿纳税、交纳资源;在支出方面,民主及其伴随的监督机制能够使国家合理支出资源、满足民众需要。
讲座最后,邓正来教授对菲利普•施密特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广大同学的积极参与表示了感谢。据悉,施密特教授已于2010年9月6日和9月24日分别在吉林大学和南开大学进行了两场演讲,此次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是其在中国高校巡讲的第三站,11月初他将赴浙江大学进行第四场演讲。